 魏京生原是文革造反派“联动”成员 参与过抄家和打斗
魏京生原是文革造反派“联动”成员 参与过抄家和打斗魏京生在美国四面树敌
仇视克林顿及民运代表人物
子夜,美国9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辆小车以超过100英里(160公里)的时速向南急驶。驾车的是以“保外就医”为名定居美国的中国前政治犯魏京生。车是借来的。魏京生不停地看看后视镜,对同车的其他人说,“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踪我。”
已经五十岁的魏京生每晚睡眠不过5小时,但烟是一根接一根、一盒接一盒地抽,不管品牌。
魏京生只用两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即从纽约开到华盛顿,一般人需要4小时,因为在他看来,追击他的人可能潜伏在任何路口,而这些追击者可能是曾将他关进条件残酷的监狱18年的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柴玲、鲍戈、王希哲、王炳章、王军涛、王若望等(魏京生称他们为“疯狗”,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原先为他提供住房的哥伦比亚大学已在赶他离开校园(魏京生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可能是克林顿政府,尽管白宫曾在1997年欢迎他出狱,魏京生说,“他们现在希望我还是死了好”。
魏京生断定,最近,他出了一系列交通事故,罪魁就是这些人。
魏京生的车风驰电掣,路边的交通标志一闪而过,上面的文字他多半看不懂。
1997年,魏京生出狱后来到美国时,台湾陆委会及美国国会的个别议员曾寄希望于他对北京当局的控诉有助于加强国际舆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声浪。然而,时隔不久,他的狂妄和无知便使几乎所有在他来到美国后见过面的人士都与他如同陌路。
由“中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推荐给魏京生当助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David Welker说,“人们觉得,魏京生已与整个世界对立。”
魏京生在中国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作为北京动物园的电工及“文革”极端组织“联动”的基层成员,其见识的浅薄和言谈举止的粗鲁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他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鉴于此,现居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曾一再劝告他抓紧时间补习初中文化课程,并多看些书籍,增长知识,以免对公众发言时贻笑大方。然而他觉得这些忠告实际隐含对他的“羞辱”,心生恶念欲图报复。
当有人问魏京生解决中国政治专制体制的办法时,他会不假思索地说:“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我们曾告诉魏京生,‘这已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们所说充耳不闻。魏京生已不太为人们重视,因为他的观点已与政策问题不相干。 ”
从那以后,桀骜不驯的魏京生与朋友们的关系一个一个地闹僵,政治联盟也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毫不掩饰地抱怨,除了几名领取台湾情治机构津贴行事的人士尚能与他“合作”之外,海外民运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将他逐之门外。更令白宫气愤的是,魏京生出于强烈的妒忌心竟当众诽谤声望远盖过他的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徐文立、王有才。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另一名中国前政治犯王希哲,为此向纽约法院以诽谤罪起诉他。
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给魏的公寓里,地上散满了书籍(大多是用他看不懂的语言出版的,放在房间里仅作为装饰),烟灰缸中的烟蒂、烟灰越堆越高。魏京生在那里一遍遍向来访的记者解释,为什么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是他的敌人。魏京生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为什么我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魏京生说,“我当克林顿是我的敌人,克林顿也把我当他的敌人。当然,他不便直接说,但他指使别人叫我闭嘴。在中国,他们简简单单地将你关进监狱;在美国,他们总有其他办法控制你。”当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政治人物不愿见他时,魏京生相信,他们都是听命于克林顿----一个支持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人。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魏京生当敌人。至于魏京生说,美国政府希望他还是死了好,国务院官员说,“他当然有权随他说,但设计交通事故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事办法。”
光著脚,穿著T-恤的魏京生,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形同马桶的打火机,出示给记者看,说:“中国制造,”接着他便打开话匣子,重复那些至少已被他说过好几百遍的话:“人们问我是否恨邓小平,我说,‘不,恨他干吗呀?我恨的是那些被中国政府折磨却还替中国政府作帮闲的人。’”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是谢万军和王丹,因为他们都支持白宫决定实现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
1999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情况简报会议中,他与中国流亡民运人士王希哲、薛明德等推推搡搡,高声叫骂,并指王希哲为间谍,结果王希哲愤然以诽谤罪将他告上法院。同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再度让满屋子的中国问题学者目瞪口呆----他大喊:“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魏京生说,“虽然没有不容置疑的办法证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可以以此透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魏京生几乎与所有中国流亡政治异议人士闹翻,甚至成为永久的敌人。刘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的老友,如今受雇于美国“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他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已没有任何关系。”
1998年,加州大学大伯克利分校邀请魏京生前往该校完成狱中回忆录。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烟,然而爱烟愈命的他却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经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报器大作。6个月后,他被撵了出来,其时他的回忆录尚未完成。
哥伦比亚大学给他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保健,还为他妹妹魏玲提供英语辅导,但该校最近已要求他在明年6月之前 搬走。“人权观察”组织的创立者Robert Bernstein说,“魏京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什么也没干,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
接受台湾陆委会津贴的魏京生现在花大量时间在中国问题上游说那里的政治人物,呼吁美国支持台独和藏独,但他的个人见解往往与政治现实间的存在巨大反差,而他丝毫不在意这些。当穿著宽松的蓝短裤、皮凉鞋,拿著香烟的魏京生姗姗来迟地走进会场时,人们多半都不愿搭理他。
前不久,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与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交手----他在那里使用信用卡购买一宽屏幕彩色电视机被拒。魏京生说,“他们又在跟我捣鬼。”他断定,中国的特工曾在他的信用卡上作手脚。
目前的孤立处境没有让魏京生倍感烦恼。不过他仍试图说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话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同时安慰自己,比如,他会说:当中国共产党政权崩溃,他当选总统时,历史将证明他魏京生是对的。魏京生的结束语通常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译自2000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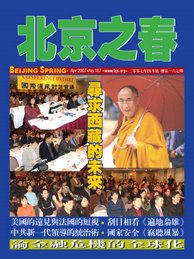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